另一变化是,五年前,上海还没有开通高铁。现在可坐高铁。至上海,我入住的是复旦皇冠假日酒店。上次来复旦,也是这家酒店。但那次我与飞氘同居一个双人间。这次,是单独一室,且是商务套间,有各种额外服务。
十二月二十七日的讲座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举行。哲学课堂是复旦大学哲学系面向公众举办的一场思想大餐,听众是要交钱的。我看网上,有七百元一张票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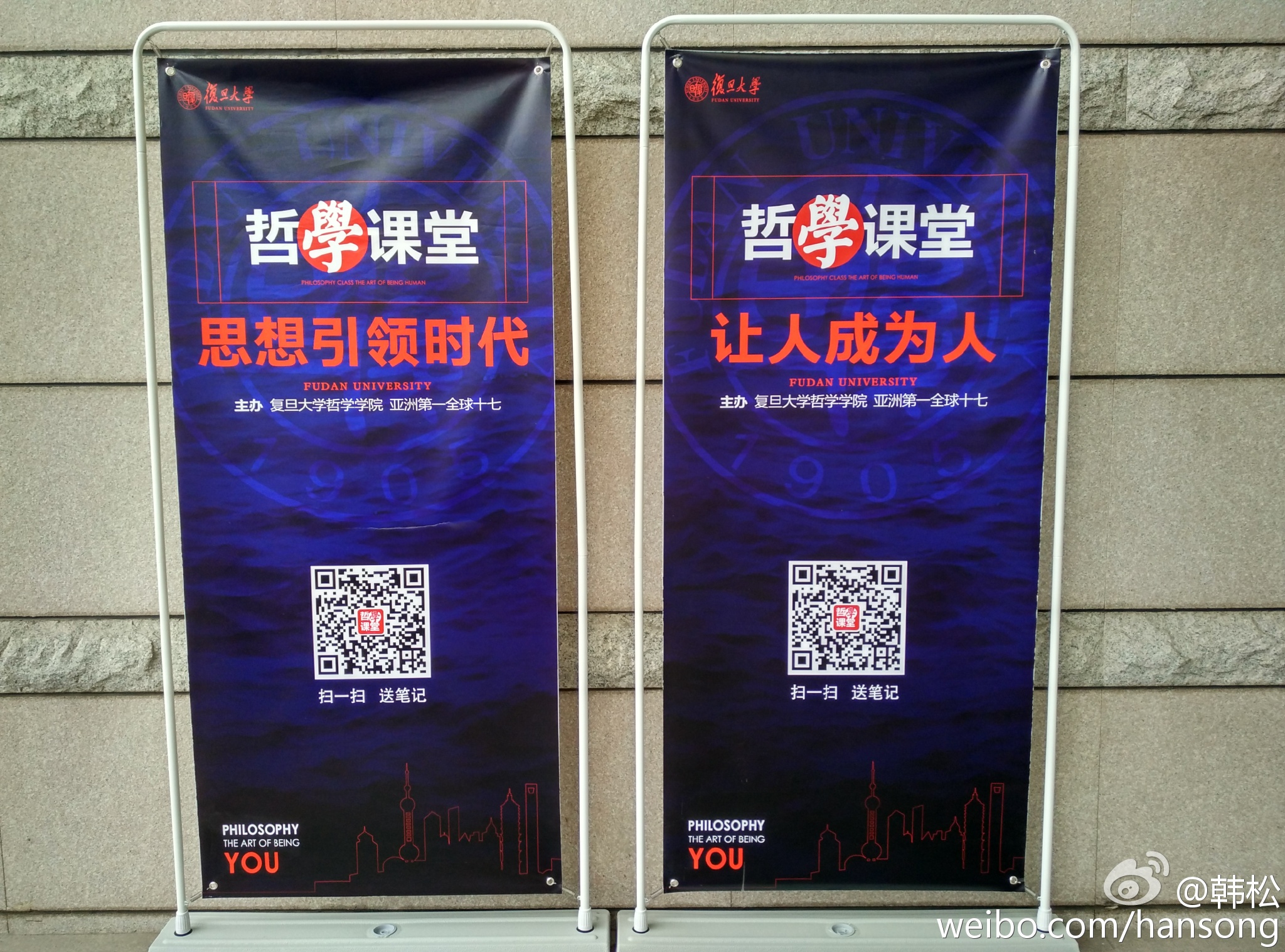
讲堂里坐了约三百人。都不是传统的我熟悉的科幻迷。以前我主要与大学生、小学生交流,以科幻迷为主。但现在这些人,都是成年人,中年人为主,衣冠楚楚,很体面的样子,很多人没有接触过科幻。据说有投资家,有读MBA的,有做实业的,有教授,有社会上对文艺感兴趣的“老克勒”。我嗅到一种变化的气息。
讲座开始时,我说,科幻本来是小儿科,胡思乱想,是不正常的、精神有问题的人才去关注的。感谢吴岩老师,提升了科幻的品味,他从今年开始做世界上唯一的科幻博士教学工作,本来,是他要来讲的,但因为生病,临时换了我。如果他或他培养的学生来做讲座,会比我好上百倍。
总体上看,大家对我的演讲比较欢迎。但在最初半小时里也有五六人退场,而且有个人在讲座开始几分钟后就睡着了,发出很大的鼾声,这让我从那时起便失去了状态,一直到结束都没有恢复过来。但大部分人很好,多次掌声,笑声,非常礼貌,客气。而且最后踊跃提问。
我说到上海诞生了中国本土第一个科幻小说,拍了第一部科幻电影,出版了至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小说,还第一次把科幻作家请到了哲学课堂。大家又鼓掌。
我讲了科幻的起源和历史,它的意义,中国与科幻的关系等。我想说明科幻是一种颠覆性的东西,它有哲学意义。这些都是中国的创新驱动需要的。但科幻本身并不是功利的。
最后的提问环节,因为我拖时了,主持人只让三人提。有个人问,霍金为什么会对科技的未来担心。现在是否更加分散化、去中心化,由大众决定。还提到了凯文凯利。另一个人问,有的科幻把世界写得黑暗,为什么。还有一个人希望了解我的日常生活,以及科幻灵感来自哪里。
十二点过了,不少人不去吃饭,围着我继续提问,要加我微信。与传统科幻活动不同的是,没有一个人要我签名。
有个做零售业的是从深圳赶来的,她讲到,科学、科幻与平时工作看似无关,但是,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科技带来的变化,她很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有一个做风投的,希望我能帮助他分析,未来的哪些比较科幻性的领域,可能成为投资的方向。还有一个是IBM做大数据的,与我谈到了人工智能。
复旦校园里,还看到了陈思和老师的一场科幻讲座的广告。

我感到中国一些地方可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场域,正在改变一些东西。这包括最近在深圳举办的晨星晋康奖。那里一些人今年自发成立了一个叫科学与幻想成长基金的公益组织,无条件支持科幻发展。这在中国也是第一次。
还有就是十二月发射了中国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。这是中国第一颗真正意义上做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实验卫星。以前的主要满足生存,达到直接的经济和军事效益。
中国是不是来到了一个节点呢?有的人看起来正在超脱日常生活的东西,开始思考和关心终极命题。可能这个变化到来时,中国的经济也好,生存也好,它的质量会有提升。这首先发生在上海、深圳这些海派城市,思想文化领风气之先的地方,没有那么多束缚的地方。
中国要解决它的问题,可能最终还是在思想和文化领域。我从这次复旦讲座中,看到了一种文艺复兴般的悸动,也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现场。但真的是这样的吗?我常常又很困惑。
接着参观了龙美术馆。在上海,私人美术馆的兴起是一个特别的现象。龙美术馆是由造船厂船坞改建来的。这颇有象征性。展览的是亚洲艺术家的现代主义作品,题目是“想象突围现实”。 第一次,我看到了石田彻也、村上隆、草间弥生的原作。

还有岳敏君。同行的上海朋友说,可不要像他那样,从一个话语体系中逃出来,又掉入另一个话语体系哦。艺术就是要创造自己的新东西。
复旦的系列讲座还有一场是讲量子论,提到了确定性的终结。
回程我坐动车,有熟悉的陌生感。包厢里,对面两个女孩,大冬天穿得很少,有个还是迷你短裤。其中一个上车就说想抽烟了。
中国正在呈现多样性,这是有意思的,也使得很多仍不确定。新年在不确定性中走向确定,同时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。再要把它弄成一元化,不可能了。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